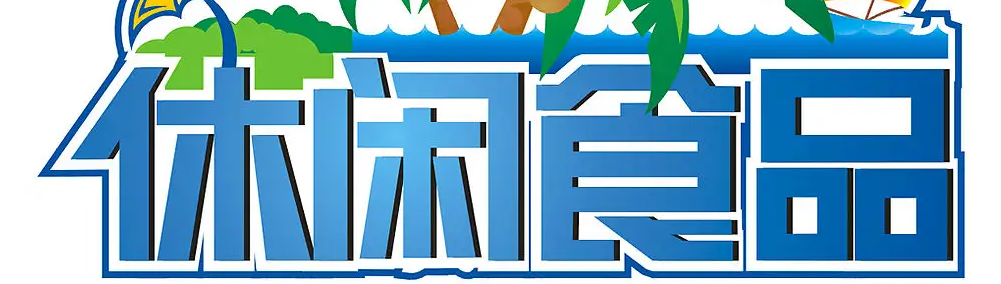蜜饯品种的丰富程度,与一个民族的味觉系统精细程度和口感多元化密切相关。有中国人的地方,任是盛世荒年,蜜饯都不曾被冷落,其杂陈的五味实在能解华人冷不丁袭来的某种馋。
曾有学者提出蜜饯起源于商代的说法,但当时主要将盐渍梅子作为调味品,也算不得真正意义的“蜜”,只能算“泛蜜饯”。东汉《吴越春秋》的“越以甘蜜丸欓报吴增封之礼”据说是有关蜜饯最早的记载。
也有种说法:蜜饯的起源与杨贵妃密切相关。贵妃酷爱荔枝,可从蜀地到长安即使快马加鞭也保不住鲜果的寿命,于是催生出蜜煎荔枝肉的防腐技法。
唐宋时期蜜饯已然形成了成熟完备的加工工艺技法。随着重商政策的推广、市民阶层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宋朝出现了我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的高潮。还专设了四司六局以供达官贵人们承办各种庆典和宴席。当时制糖工艺发达,六局中专设“蜜煎局”研发、采办各色蜜饯。
后来蜜煎演变成蜜饯。苏轼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那便是北宋的蜜饯粽子。在两宋文人的散文中,蜜饯也无处不在,仅在商肆中售卖的干果蜜饯就有三十多种。
酒肆茶楼、夜市勾栏、庆典祭奠,在在处处,皆有蜜饯,蜜饯是那个时代深受市民特别是文人雅士追捧的零食。是开胃小食、餐后甜点,也是社交工具。从上层到市井,可谓全民风雅。
在明朝世情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和友人吃酒时配了几碟果食,其中就有“衣梅”,“犹如饴蜜,细甜美味。”在这本书中,茶事有多达七百余处,茶楼茶肆遍布城中大街小巷,饮茶不是清饮,而是搭配荔枝干、杏干、桃干等蜜饯和饽饽、火烧等茶点,还有蜜饯金橙泡茶等花式茶饮,品种丰富,情趣盎然,表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业态与社交方式。
明朝中期以后,杭州蜜饯风靡两京,随着京杭大运河运往繁华的苏州、南京,然后一路北上,进入京城。
晚清的满汉全席中,也有由桃脯、蜜枣、藕脯、荸荠脯等谓之“糖饯”的蜜饯组合。
上世纪初,有千年技艺传承的北平“聚顺和”蜜饯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击败日本福神渍和法国台尔蒙罐头,获得金奖。而聚顺和就是北京市果脯厂的前身。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迭代成为红螺食品集团。最知名的就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古早蜜饯:北京果脯。
老北京果脯的制作技艺可追溯到明清时期,脱胎于宫廷御膳。2020年,北京果脯的制作技艺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印象中,北京果脯大而甜,单个足有半两重,呈椭圆形,含糖量和含水量都不低,多用那些“广谱”的水果制成,苹果脯、梨脯、杏脯、桃脯、海棠脯等,品种较少,口味酸甜,以高浓度的糖液为保藏依据,以烘干为主。著名的有红螺和御食园等。在我童年时代刚刚改革开放,物质水平较低,北京的零食代表仅有果脯和茯苓夹饼,可口度终不能与南方吃食同日而语。
南方蜜饯则多用梅子、李子等杂果或陈皮等果子配件,以甘草、糖盐和一些添加剂为口味支持和保藏依据,滋味千回百转,耐人寻味。
其实广式凉果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制作技艺已成为广州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方蜜饯著名的除了广式凉果、苏式蜜饯外,我尤爱以咸、酸为主并加入各种中药材的闽式蜜饯(比如青津果、八仙果)和饱糖饱水、滋润化渣的内江蜜饯(比如糖渍金桔)。这几味蜜饯,倒是有几分时髦知识分子的调性。
去福建时,酒店自助餐里也常有蜜饯与腐乳、酱菜等放在一处,那些滋味复杂的蜜饯很是开胃,常以配粥小菜论之。
读小学时,广东凉果多来自潮州庵埠,这地名曾一度让我以为那是一座庙。我的零食罐子里常常塞满了话梅、橄榄、甘草芒果、九制陈皮、半话李、九制山楂等。
记得我十一二岁时,爸爸去某宾馆开会时带上了我。他开会时,我在大堂看绿毛龟。傍晚开席,先上十碟蜜饯,我左右开弓大快朵颐。待到冷盘热菜各就各位,长辈们把我的碟子摞成一座山珍海味的小山时,我的胃纳已基本被蜜饯塞满。
那夜盛宴,菜式精致,氛围高雅,可不开眼的我浪费了难得的宴饮机会,却饱餐了一顿登峰造极、刻骨铭心的蜜饯大餐。
比起苏式蜜饯的绵甜,我更喜欢广式蜜饯入口时的刺激快意。采芝斋名气大,蜜饯价格比庵埠凉果高得多,可年少时我无法体会它的好处。然而外婆是采芝斋的忠粉。她坚持采芝斋的苏式话梅好过广式话梅数倍。
外婆生于旧社会,年少和年轻时曾过着肥马轻裘的日子,对于吃,她很有审美力。她说人老了,口味趋淡,更中意悠长。我似懂非懂。但见她推牌九时口里还含一颗苏式话梅,一粒线岁以后能约略体会她那个“淡”的意味时,她老人家已经作古多年。
生于上海、祖籍苏州、有一半绍兴血统的他说这是句绍兴老话。绍兴人是否爱吃橄榄我没考证过,不过绍兴人吃茶民俗中爱放一颗青橄榄我也是感受过的。
包括上海在内的整座江南都是爱吃檀香橄榄的。小学时第一次吃檀香橄榄的情景宛如昨天。爸爸买了一纸袋青橄榄,一边骑自行车载着我,一边共同品尝。我初尝只觉得含有少许汁水的橄榄又酸又涩,口感粗糙略苦,爸爸说,别急,马上就是雅致的回甘了。果然橄榄在青涩的低回后转瞬婉转清扬。爸爸还经常拿一撮龙井茶和两颗檀香橄榄置于白瓷杯中闷盖片刻后赏味,有别样的清芬,于是我从很小就开始喝这种古早味绿茶了。小小的青橄榄貌不惊人,但滋味独特带劲,是一种遗世独立的清雅存在,多咀嚼才能辨出它的曼妙不凡,且能清热利咽。
至今我都是橄榄的拥趸,生吃、蜜饯、入馔、入茶、入汤无一不喜,拷扁橄榄,盐津橄榄、甘草橄榄、陈皮榄等,是办公室零食的“常在”。很喜欢以竹壳缠红线、每根竹节般缠出三四粒橄榄的包装,以小捆出售,很是喜气,商标常以某某行命名。还有以陈皮裹咸橄榄被禾杆草扎紧的广东三宝扎,陈香醇厚,咸香中和,能荡涤烦渴,醒神解腻。
橄榄变幻成橄榄酱抹法棍、变幻成橄榄菜过白粥、蒸鱼、变幻成南姜咸甜橄榄糁也都能让平凡的食物点石成金。
在我看来,橄榄的味道也分前中后味,余味缭绕,沁人心脾。江南人不算是中国人中最爱吃橄榄的,但一定属于比较爱吃的。橄榄真正的老饕在闽南,在广东潮汕。这可能也与他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常常迁徙有关。淡味咸橄榄能防止晕车,而全咸橄榄炖汤、配粥,是最好的调味品。在他们眼中,橄榄咸是咸味的另一种载体。出远门时,行囊里一定会有一袋橄榄,乏了,油腻了,想家了,就会嚼上几颗,那是故乡的水土。
再说说粗人为什么不吃橄榄,相比于橄榄的层次感和韵味,粗人可能更爱奶糖的直白。不过精细化思维是江南人的本能,细在游戏规则、人心沟壑和文化自觉。其中自称粗人者往往更值得思忖玩味。他们通常不会是真正意义的粗人,只是把细糠藏得比较深而已。而为追求表面精细用力过猛、忽略了真正价值感的打造与夯实,才真正是拎不清的粗人了。
想到台北,我最先想到的不是101,不是圆山饭店,而是大稻埕迪化街。那是正宗老台北、最台北的所在。曾是台北买卖茶叶最重要的商港。港边洋行林立,是台北早期接触西洋文化的区域之一,百年前也曾是北台湾最热闹繁华的富庶之地。无论是中式、日式、西洋式混搭的特色建筑,还是传统民俗、南北货、参药行、本地美食云集的生活业态,迪化街四处洋溢着老台北城的历史轨迹。那里的南北货和中药材琳琅满目,层次分明、鞭辟入里,每寸立面都恣意汪洋的展示着自家好货。过年时它也是著名的年货大街。我在那里买到过最好吃的八仙果,柚子参和台式话梅。
阿叔给我拿出藏在后店的蜜饯新货,然后分别均分三份的真心实意的神情,至今回忆犹新。五年没去台湾了,不知迪化街是否热闹如初?
度过了不平凡的疫情三年,这两年,香港的小实体再度客似云来。在零食店,内地游客常常动辄称千八百元零食,结算时店主含笑麻利地多赠送两罐腰果糖和一磅西梅塞在纸袋里。那赠送的西梅格外酸甜丰腴。我大爱“么凤”话梅王,是话梅中的爱马仕,口感扎实饱满,100元也就几颗。常有友人去香港出差公干或小住闲玩。每每他们去香港时会特地找到“上海么凤”凉果店,称上一袋话梅王,回上海后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悄悄塞给我。这些朋友,我们平时联系并不多,各忙各的,却总是个安心而稳定的存在,且梯队靠前。么凤话梅王是我们之间私密的小仪式,和温暖的线索。
当抿着那些收干却还在蓬勃呼吸的秘实果实时,我会想不能以水果的标准评价蜜饯,如同不能以爱情的标准评判婚姻。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或绿洲,好比蜜饯不是水果的衰亡或辉煌,而是一种以重生姿态表达生命活性与生机的载体,是一段抵达某处的长长的旅途。
今年大年三十,身处迈阿密的发小向我展示了他的年货:购自华人超市的烤鸭、上海烤麸和一袋嘉应子。一个大老爷们也吃上了蜜饯,这让我暗自好笑。不过,我也知道,在华人稀少的迈阿密,这袋嘉应子,就是故乡上海的符号。